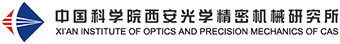侯洵院士接受采访
01
转行:国家需要就去做
侯洵是我国著名光电子学专家、瞬态光学和光电子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他从事光电发射材料及快速光电器件研究已有40余年,曾主导过多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所有这些成就,是从几十年前,领导来劝他“转行”开始的。
在那个年代,科技人员普遍认为,做理论研究,只要多看文献、多思考就可以了。相对而言,要做实验,就需要仪器设备,以当时的物质经济条件,是很困难的事情。这就造成一个当时看来很怪的现象:在我国的物理学领域,做理论研究的人要比做实验研究的人多出好多。而国际学界的常见结构是,一个做理论研究的科学家,通常需要6个或更多做实验和工程的研究者支持。
侯洵原在1958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西安原子能研究所做有关磁约束受控热核反应方面的理论工作。1962年随该所进入新建的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西安光机所”)不久,领导便找他谈话,希望他能从理论研究转向实验研究。
尽管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跨度较大,但侯洵当即表示:“做实验就做实验,这是国家需要!”
转行之后,侯洵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便是研制克尔盒高速相机、并从此进入瞬态光学领域,参与研制了一系列电光与光电子类型的高速摄影机,包括电视-变像管高速相机及光纤-变像管毫微秒扫描相机、多种超快过程研究用的可见光皮秒扫描相机、X-射线皮秒分幅与扫描相机等。
这一系列超高速瞬态现象观测设备的研制成功,使我国超快现象研究的时间分辨率从微秒进到了皮秒,提高了六个数量级,赶上了国际先进水平,多次成功应用于我国大型试验及相关科学研究。
02
创新:“独家定制”科研设备
侯洵的科研生涯,是从一穷二白的年代走过来的,因此对创新,他有着格外的重视。他认为,科研人员自己研制仪器设备,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独特的设备,才能做出创新的工作。
侯洵年轻时,由于实验室的条件非常局限,自制实验设备可谓家常便饭。例如,他们研制克尔盒相机需要制作克尔盒。所谓克尔盒,是一种内装一对电极板并盛有硝基苯液体的玻璃盒子。实验有个步骤,需要用火焰将光学质量的玻璃窗片熔化粘接在盒体上。
但在当时,西安没有煤气,侯洵和他的同事们就找来一个汽油桶,内装部分汽油,通上两根管子。一根管子插进汽油里,拿空气压缩机向桶里打气。另一根管子在油面之上将带有汽油挥发的气体引出形成可燃气体。
燃气配出来了,但是这个设备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一直往里打气,不仅浪费,还很危险,需要一个自动控制气压的器件。于是他们自制一根U型玻璃管,给U型玻璃管两个分支高低不同的位置,装上电极。U型玻璃管一端与汽油桶连通,管内充上适量水银,使之在未向桶内打气时能连通两个电极。电路就通了,压缩机便开始工作;等到压力加大,水银柱子又会被压到一边,从而与电极脱离,电路断开。如此循环,桶内气压便得到有效控制。
“东西虽然简单,但解了燃眉之急,保证了研制进度。”说起这些时,侯洵言语里仍然透着股自豪。
对今天的科研工作者而言,这样的实验传统早已成为过去。大多数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都可以花钱买来。但是侯洵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研制相应的仪器设备,这样做出来的成果会更有意义和原创性。”
“如果只是花大价钱买国外设备,做点‘换汤不换药’的实验,发几篇论文了事,这种做法不但是对金钱的浪费,更是对人才的虚耗。”侯洵说:“人家早都做过的事情,能有什么创新呢?又能解决多少国家实际问题?”
“自主研制”,这4个字的分量,侯洵有切身体会。1984年,侯洵与有“中国光学之父”之称的王大珩院士一起到巴黎参加国际高速摄影会议。在一间展厅里,侯洵看到了一台光纤-条纹相机,这是一台能够代替十多台高速电子示波器的设备。他向工作人员询问价格,不料对方看了他的胸牌后,说:“这个不卖给中国。”
遭遇如此无礼对待,侯洵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窃喜,因为“与这种条纹相机完全一样的设备,我们刚刚研制好,已经运到基地去了”。后来,他们自主研发的光纤-条纹相机在基地成功运行,为国家的大型实验作出了贡献。
03
情怀:愿为家国坐“冷板凳”
由于所做研究的保密要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侯洵虽然做了很多工作,却几乎没有发表过文章。默默无闻没有让侯洵沮丧:“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为国家需要服务,发不发文章,并没放在心上。”
即便到现在,曾经做过的涉密研究,仍然带给侯洵不少“麻烦”。他自嘲上了美国大使馆的“黑名单”。他每次出国,都要接受美国大使馆繁琐的面谈,经受将近一个月的审查,才确定能否得到签证。
但是侯洵从没后悔过。他说,他们那一代人,愿为国家的繁荣强大做任何事。
侯洵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度过的。西安的城墙又宽又结实,可以并排开过两三辆汽车。军队在城墙墙体上挖出大小不一、弯弯曲曲的防空洞,有供政府和军队安置电台的,有用来储存粮食物资的,更多的是供老百姓躲避轰炸的。日军的飞机一过潼关,警报就会拉响,侯洵和父老乡亲们就集体钻进防空洞里。“这就是人们说的‘逃警报’。”侯洵说。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解放前中国的积贫积弱、中条山战役时父亲的牺牲……所有这些,都在年仅十三四岁的侯洵心底,埋下了救国强国的种子。
考入西北大学物理系、进入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工作——这是侯洵选择的报国之路。
1978年,侯洵随中国著名光学家龚祖同所长带领的中国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高速摄影与光子学会议。会上,他主动找到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国际著名变像管条纹相机专家、帝国理工学院物理系主任D.J.Bredly,直言来意:“我们想派3个人到您那里习。”得到Bredly的同意后,他和牛憨笨、赵积来三人由科学院以成组配套的形式派往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习了两年。由于有在国内研制纳秒变像管高速摄影机的基础,回来之后,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属于自己的皮秒条纹相机。
上世纪70年代,侯洵负责成功研制出磁聚焦云母片耦合四级像增强器,国内首个透射式砷化镓阴极和场助光电阴极;
80年代初,侯洵发明了长波响应高、面电阻小、稳定性好的钯银氧铯阴极,参与研制成功国内首个双近贴聚焦像增强器;
1985年,他作为主要贡献人之一,以“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
1986年以后,侯洵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及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国家发明三等奖一项。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侯洵用《论一个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话来形容自己:“我们这一代人打起背包就出发,国家需要我们干啥就干啥,拧到哪都能起作用,没有什么个人前途之类的考虑。”
04
科普:“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侯洵不仅对科研充满热情,对青年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视。他培养的65名硕士生、40余名博士生,现在大都成了瞬态光学或半导体光电子器件领域的科研骨干。
卸任所长后,侯洵响应国家号召,开始做培养青少年科学知识兴趣的工作。他结合自己的专业及经历,先后在西安、汉中、商州、咸阳等地的中学、大学作过多场科普报告。近年还去过重庆市的西藏中学和彭水中学为少数民族学生作科普报告。
他最爱讲的故事,是高速摄影机的发展。人们对高速摄影机的“快”,有着永无止境的追求。对于传统的光机结构的间歇式高速摄影机而言,拍摄频率的快慢,取决于底片一停一拉的速度。受底片抗拉强度的限制,全世界的技术水平,基本能达到每秒钟360多张。但人们还想更快,该怎么办呢?
人们想出了一个“相对静止”的办法:让底片匀速运动,而在光学系统中加一个可旋转的棱镜,调整棱镜转速可保证在曝光的瞬间,底片和图像是相对静止的。这样不仅速度上来了,成像也是清晰的——这就是棱镜补偿式摄影机。这一技术让分幅摄影机的速度提高到了每秒钟1万张左右。由于将底片由静止加速到一定高速需要耗费大量底片,因此拍摄频率的进一步提高受到了限制。
还要更快,人们是这样设计的:光学成像系统经过可以高速旋转的镜子反射再成像,将底片沿着成像的轨迹,也就是说轨迹的这一周都是底片,再加一个旋转的镜子,前面的光学成像系统经过可以高速旋转的镜子反射再成像。照到底片上,这样镜子转得快,拍摄速度也就更快,最高达到了每秒2000万张……
一年又一年,经历了一次次的“开路”和“架桥”,高速摄影机的分辨率从皮秒、飞秒直奔阿秒。侯洵用科学家们追“光”捕“快”的故事,鼓舞了许许多多青少年。
“我觉得年龄大一点的科研工作者,有责任传播科学知识,激励年轻人。”侯洵说。
在科普报告的最后,他常以“珍惜时间”结尾。鲁迅在论及很多人常常遇到问题说没有时间想时说:“不是没有时间想,是有时间的时候没有想”,侯洵一直把鲁迅这句并不那么有名但却充分体现了辩证思维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利用时间充分思考自己的各种业务,就不会在问题来临时手足无措。”

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侯院士
寄语:这是创新突破的最好时期
或许是亲历了国家最危难的岁月,见证了国家从弱到强的艰难创业,侯洵对年轻一代有着更多的希冀。他总是说,年轻人现在正处于最好的时代,要志存高远、珍惜时间。
侯洵刚刚参加过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两院院士大会,感触颇深。他认为,青年将在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科研人员来说,现在是创新突破的最好时期,也是距离振兴中华这一目标最近的时期!”他嘱咐国科大的学子,一定要认识到,自己已经处于科研人才层次的顶端,要有相应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侯洵认为,一所大学,培养人才是第一位的:“中国科学院大学除了为中国科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人才,更要为全国培养出顶尖人才。”
经历过先后“跟着苏联和英美走”的年代,侯洵更迫切地希望,在这最好的时代里,我们国家的科技能够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跟随走向引领,昂首于世界科技之林。
采访中,侯洵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在他的描述里,那个年代的人,为自己想得很少,为祖国想得很多,只要是国家的需要,他们总是二话不说地担起重任。
那个年代的人,说起“民胞物与”,谈起“家国天下”,都是出乎自然,全无大话。那个年代他的父亲,在为国而战的疆场上捐躯;那个年代他的母亲,常常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告诉他“忠孝不能两全”,勉励他专心做好工作。
他爱读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传记,居里夫人的故事对他影响至深:“居里夫人发现了镭,提纯出来后可以治疗癌症。若申请专利,必获大利。但她却认为这是属于全人类的,应为人类造福,故而没有申请专利。她由于长期从事放射性工作,患上了白血病,定期换血可以延长生命,但她认为她不能老拿别人的血来养活自己,最后因为拒绝换血而辞世。”
在他的回忆里,那个年代的物质很贫乏。好不容易完成一项科研任务,项目结题验收时,不光成果被运往试验场,连辅助仪器设备也都运走了,然而他们并无怨言,因为这是国防建设的需要。
但是那个年代,不知为何,令人神往。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心念念的,不是考试、就业、出国、买房。在更狭小的斗室里,在更破旧的书桌旁,他们怀揣的,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深情和挂牵,是对整个国家复兴的抱负和信念。
那是一个一穷二白,却又干净开阔的年代。